九死一生: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幸存者回忆录
 冷炮历史2021-11-25 07:52
冷炮历史2021-11-25 07:52
本文由公众号“尼伯龙根工厂”授权发布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威廉·格雷克(Wilhelm Gerecke)是一名无线电操作手,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在国防军第71步兵师第171炮兵团第2连服役。
1942年11月,苏军在卡拉奇附近对斯大林格勒完成合围,将德国第6集团军困在里面。彼时,包围圈中诸君还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过不了多久就能解围。我们第2连1排的人之前休假去了,那时候还没来得及赶回来。2连的炮火观测哨设置在伏尔加河畔教堂附近一处建筑物里面的浴室里(注:高层建筑物的浴室或卫生间比其他部位要更加结实一些),这里之前也曾被苏军当作指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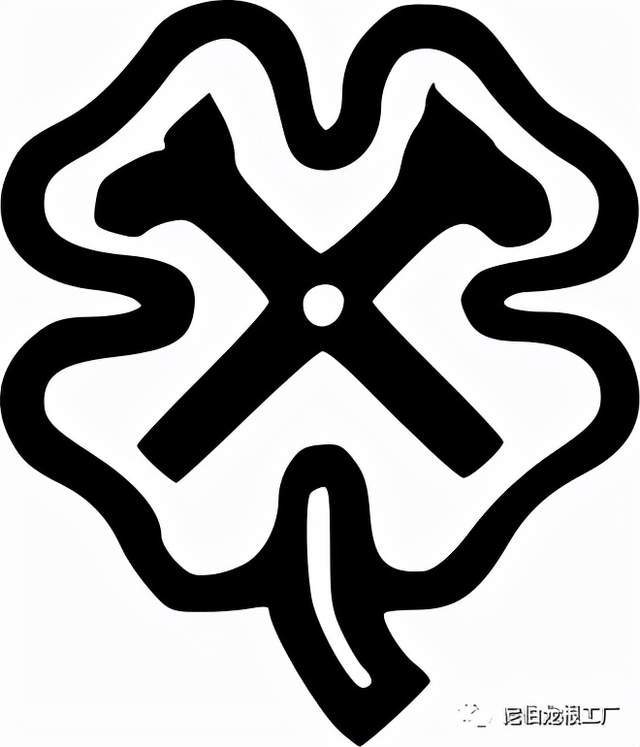
国防军第71步兵师又称“四叶草”师,1939年8月组建,兵员主要来自下萨克森、汉诺威、海德斯海姆、布伦瑞克和哈兹等地。该师先后参加过西欧战役和苏德战争初期的基辅战役、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该师是最晚投降的德军部队之一,直到1943年1月31日才放下武器。1943年中旬,第71步兵师得到重建,在意大利作战了较长时间,后来退入匈牙利参加了“春醒”行动,最终在奥地利向英军投降。
观测哨的视野非常好,能看到伏尔加河对岸老远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甚至能看见对面的苏联人正在把火炮往前推。我们的连长乌斯特尔中尉(Wüster)也去休假了,他的职责先是由海德布兰德中尉(Hildebrand)代行,没过多久,海德布兰德调任营副,又由比戈尔中尉(Biegel)接手。

乌斯特尔在浴室那里一直战斗到1月31日才向苏军投降,后来服了7年苦役。1950年获释回国之后,乌斯特尔学习法律,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一名律师,2017年去世。乌斯特尔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书名叫《斯大林格勒的炮兵》,他同时还是一名古帆船模型爱好者。
我是观测哨里的无线电员,差不多每隔十天,斯佩希特军士长(Specht)就会带着三个人上来一次。离观测哨最近的苏军阵地就在15米开外的谷地之内,交通壕一直修到火车站那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观测哨尽收眼底,所以,那里经常会遭到迫击炮弹的袭击。2连里只留下了一些关键人员,其他的人都被调到1连去了,1连那时候已经没有炮了,被当作步兵连部署在伏尔加河畔的阵地上。
12月17日,上面下达命令,要求摧毁所有非作战必需的武器装备,我们只留下了两门炮,把它们拖往南部防线,包围圈中尚存的装甲部队正在那边集结,准备向第4装甲集团军的方向突围。然而,还没等我们把家当破坏殆尽,命令就撤销了。

根据乌斯特尔的回忆,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他的2连装备了两门苏制76.2mm野战炮。1942年10月,这两门野战炮将伏尔加河上的一艘“装着两个T-34炮塔的炮艇(BK-31内河炮艇)”击沉,炮手们因此获得了铁十字勋章。根据苏联方面的消息,炮艇上只有3个人生还,后来都被枪毙了。这艘炮艇直到2017年才打捞出水,经过整修后放在伏尔加河畔展览。
12月末1月初的时候,乌斯特尔中尉从外面飞回了包围圈里,在他回来之后,比戈尔调去领导营部连。当时的营长是拉格纳上尉(Langner),营指挥所坐落在一座炼油厂里,炼油厂旁边是从市中心广场通往飞机场的公路。
1943年元旦那天,我被从炮火观测哨调到了营部。那时候伏尔加河一带相对比较消停,德军火炮的开火受到了严格限制,只能在得到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向肉眼可见的目标开火,每次开火最多发射三枚炮弹。与德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岸的苏军炮兵只要看见一个人影,就会动用一整个炮兵连炸个没完。地面已被厚厚的积雪覆盖,还结着霜,气温只有零下二十多度,头顶的苏军飞机一刻不停地飞来飞去。

乌斯特尔的水彩画,伏尔加河畔的德军炮位。
营部被当成了卫生所,里面挤满了伤员。那里本来立着一个巨大的红十字标识,非常醒目,但苏联空军却对此置若罔闻,干脆投下白磷弹把红十字烧了个精光。在城外的草原地带,苏军的包围圈收得越来越紧,大量的残兵败将被迫退入城内,营部这里乱糟糟的,哪个师的人都有。这时候,最辛苦的人莫过于我们营的亨斯特医官(Hengst)了,大家怕医生们累垮,都纷纷省下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口粮送给他们。
1月20日,在团长冯·施通普夫中校(von Stumpff)、团副施密特上尉(Schmidt)的带领下,团部指挥所也转移到了我们这里。28日,苏军已经抵达伏尔加河南岸,我们和南边友军的联系被彻底切断,扎利扎(Zariza)那里的格别乌监狱已经塞满了德军战俘。这天晚上,团副和其他几名军官试图带人突围,想要顺着伏尔加河往高加索那边走,后来杳无音讯(报称失踪)。

1月29日,我们把指挥所里所剩无几的一点罐头瓜分一空,肉食已经在前一天晚上分光了。这天下午,一辆四号坦克出现在街道上,对着苏军步兵和迫击炮阵地开火,苏军动用火炮还击,一部分炮弹落在了我们的指挥所那边。团长和营长都死了(可能是自杀了),天黑之后,剩下的人转移到了一处地下室里,在地下室里躲避炮火的人员成分非常复杂,其中甚至还有一位来自空军第3“乌德特”战斗机联队的飞行员。德军的第一道防线已经工事化了,非常结实,苏军不敢在晚上进攻,从两边绕过了它,因此,在我们这里又形成了一个小包围圈。

乌斯特尔的画作,当他(右一)回到指挥所的时候,团里和营里的各位领导们都已经喝得烂醉如泥,嚷嚷着不想活了。
子弹打光了,我们把枪也都给拆了,没有必要再战下去了。1月30日,我们向苏军投降,在被押过苏军防线的时候,那些苏军把香烟和雪茄送给我们抽,一看全是从德军仓库里缴获的。
苏军的前线部队没有怎么为难我们,还和我们说:“战争结束了,你们可以回家了(Woina kaputt, skora damoi!)。”之后,他们把每250名战俘编成一队,每队由一名看守向南押送。走出去1.5公里之后,看守换班了,新来的看守对德军战俘大肆洗劫,能抢走的都抢走了,连围观的苏联老百姓都上去薅羊毛,何等耻辱。经过这番洗劫之后,我们又被押到通往别克托夫卡(Beketovka)的公路上,一支摩托化部队接管了我们,这帮家伙开着车横冲直撞,好多人躲闪不及,都被他们撞翻了。

苏军士兵在“招待”德军战俘抽烟。
又往前走了几公里,我们被赶下公路,往铁路线那边走。晚饭是在道班房里吃的,一人分到一条腌鲱鱼,还有八分之一条面包,这就是接下来8天的全部口粮。之后,我们又被赶回公路上,那里已经有另外一支苏军部队等着我们,他们把我们最后一点“财产”打劫一空,有的人连靴子都被抢走了,只能光着脚站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地里。这天晚上,我们抵达别克托夫卡战俘营,被关押在没有窗户的营房里,这里倒是有个厨房,但战俘实在太多,吃的根本就不够,只有走运的人才能抢到一点点食物,然而,只靠这么点东西却得坚持一个星期。很多人都饿死了,营地里有两辆缴获的欧宝闪电卡车,一天到晚不干别的,就是把一车一车的死人往外拉,然后再丢进战俘营附近的沟里。

俄式腌鲱鱼巨咸无比,是苏俄时期的常见副食。
2月末的时候,德军战俘又被赶上火车。闷罐车厢里装上了木板床,地板上锯开了30x30cm的窟窿,权当厕所使用。在车厢角落里装着一具小火炉,还有一些木柴,用来劈开木柴的是一把钝得不行的小斧子。每节车厢里都塞进去了80-100名战俘,每人又分到了一条腌鲱鱼,两片面包,一路上都不给水喝。列车每次到站,都会从车厢里抬出一些死人,丢到铁路路基下面。我们这批战俘的目的地是原伏尔加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的“鲍尔”营和“诺伊曼”营,战俘们从火车站走向营地,那些不能走路的战俘都被装到了牛拉雪橇上,妇女们赶着雪橇把他们拉到营地,她们其实也是“鲍尔”营的囚徒。“鲍尔”营原本是一座整洁美丽的村庄,当地人都被强制搬迁到别的地方去了,村子被重新划分成几块营地,里面塞进了上千号人。斑疹伤寒和痢疾在战俘当中流行开来,外加营养不良,每天都差不多要抬出去二三十口子。在刚到营地的那段时间,所有人都病得没法劳动,营地里根本没有医生,全部的医疗力量就只有一名俄国护士。

苏联内务部队正在驱逐伏尔加德意志人。伏尔加德意志人最早是沙俄叶卡捷琳娜大帝召来的德意志移民,自从18世纪就一直生活在那里。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认为这些德意志人可能会支持法西斯侵略军,于是就下令把他们强制迁移到了中亚和西伯利亚,自治共和国也被撤销。相对于俄国南部的其他民族,伏尔加德意志人素质较高,也更加吃苦耐劳,所以他们的聚居区相对要富裕一些,村容村貌也更加整洁。
1943年,“诺伊曼”营解散,残余囚犯合并到“鲍尔”营里,这时候只有50个人还能劳动,他们干的是重建集体农庄的活儿。到了9月,“鲍尔”营也解散了,在当初2000余名转移到这里的囚犯当中,只有200余名活了下来,其中只有70人还能劳动,其余150个都是病号。“鲍尔”营解散之后,这200多人又被转移到沃利斯克战俘营,继续苦熬着阶下囚的日子。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测试博客 » 九死一生: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幸存者回忆录

 测试博客
测试博客 巴高达运动:促成罗马帝国灭亡的基层社会变
巴高达运动:促成罗马帝国灭亡的基层社会变 独木难支:二战中的日本神鹰号护航母舰
独木难支:二战中的日本神鹰号护航母舰 卡特万战役:西辽崛起与塞尔柱帝国的灾难性
卡特万战役:西辽崛起与塞尔柱帝国的灾难性 短命的先驱:二战中的英军大胆号护航母舰
短命的先驱:二战中的英军大胆号护航母舰 有人竟愿意花钱请人来痛扁自己
有人竟愿意花钱请人来痛扁自己 神奇的魔法木制酒店,童话森林里的城堡
神奇的魔法木制酒店,童话森林里的城堡 超现实画作:比相机拍摄更真实的纽约地铁
超现实画作:比相机拍摄更真实的纽约地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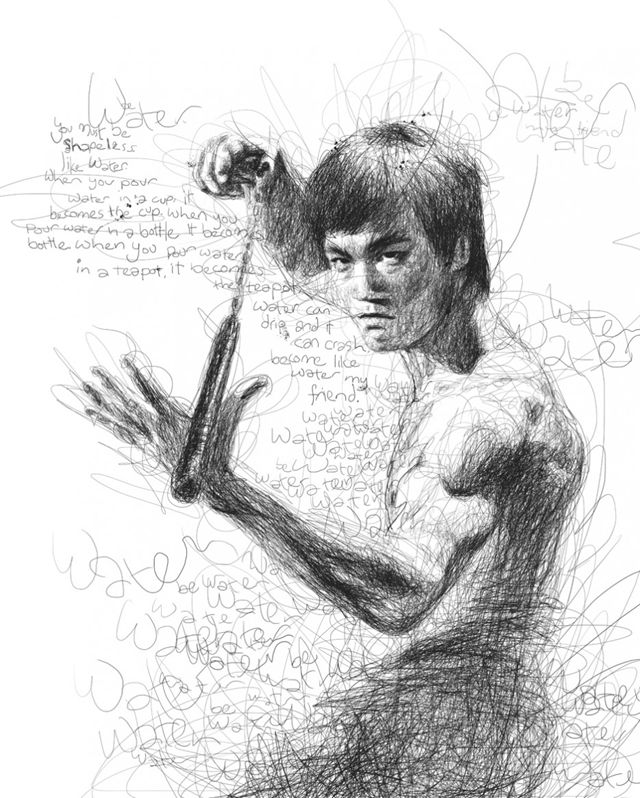 这是一个读写障碍的人画出的明星肖像,你有
这是一个读写障碍的人画出的明星肖像,你有



